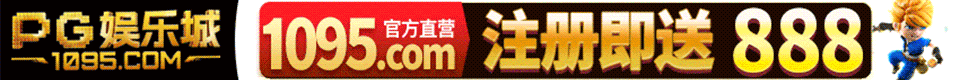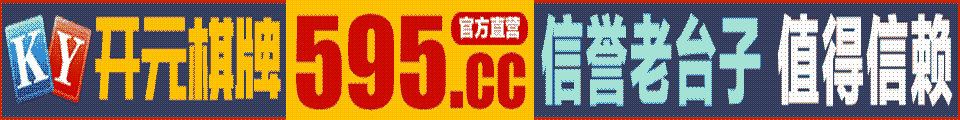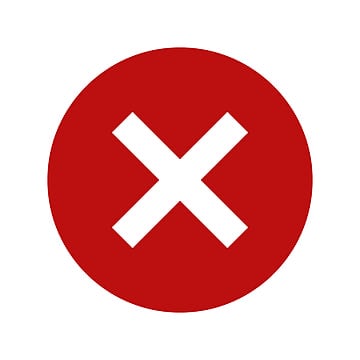走向堕落(1-10)
我叫吴晓平。当我孤寂、无聊地坐在电脑前写下往事的时候,很难说清我心里的滋味。
(一)渴望强暴
我升上高中的时候15岁,与其她低年级的小女孩被高二、高三学长追得团团转不一样的是,几乎没有一个高年级的学生注意我。我那时侯还算是一个未成年的也没有发育的小家伙,走路都不敢擡头挺胸。看到身边的小姐妹频频约会,我心痒得很,夜晚睡到寝室的床上,摸着一根毛都没长的阴户,不由得偷偷叹气。
进入高一第二学期的时候,机会终于来了一个叫孙雁南的男孩写情书给我。
他虽然很帅气、很高大,但是有些阴郁,说实话,我渴望被他强暴,被他强有力的手臂搂住一定很过瘾。可是他似乎很胆小,每次站在我一起,都不动我一下。
有一天,一个个子不高、但是更加帅气的男孩拦着我,要我说我自己的名字,我装着很羞怯的样子不肯说,他狂笑道:“我看你的胸部又小又平,就叫你小平吧。”啊?居然歪打正着。
从此,那个叫陆俊峰的男孩见到我就“小平妹、小平妹”的叫个不停,有一次他趁着停电摸了一把我还没发育的小乳房,让我几天都心神不定的。实际上,我喜欢这种直来直去的男孩,让我感觉很过瘾。而那个也许是真爱着我的孙雁南呢,连我的手都没牵过。
我听说,孙雁南是很有希望考上一所好大学的,所以不自觉的心偏向他一些,我装做无意地透漏了陆俊峰骚扰我的事情,于是他俩干了一架,孙雁南赢了。可是,他直到考上大学,都没有动过我。
(二)等待开垦
孙雁南考上大学后,不停地写信给我,可是这时的我,对于这样一个不在身边,而且根本上就没有发生肉体关系的男孩,几乎很难有感觉。这时候,一个我认识的高三学姐传给我一封信,是一个叫方叶生的男孩写的,虽然我听说这个家伙平时很花,但出于寂寞,我和他偷偷约会了。
方叶生的父母是生意人,经常不在家。一个周末,他约我去他家里,反正无聊,我也就去了。因为约会是被亲吻已是很平常的事了,所以,我一进他家,他就很粗暴地把我扑在床上,吻我,用手拼命地搓着我平坦的胸部,我的嘴虽然被他嘴唇堵住,还是不由得发出几声含混的呻吟。
他的手向下游移,插进我的内裤里。摸到我的阴唇的时候,他兴奋地抖了一下,我感觉到他压在我身上的下体有些跳动,但是我没有阻止他的动作,而是扭动着身子,轻轻地叫了一声“啊”。
大概是我的反应给了他很大的鼓舞,他解开了我上衣的纽扣,由于乳房还没有很好的发育,我没有围胸罩。他的舌头开始在我那有些发硬的乳头上舔了起来,我更加用力地扭动着,不是拒绝,而是兴奋。但是就在他要解开我裤子纽扣的时候,我突然想起了孙雁南。
这个第一次表示喜欢我的男孩,一星期写一封信给我,在信中透露出的真挚情意曾经让我的好姐妹盛余芳大加赞叹,而他又是一个那么有前途的男孩,我是没理由选择身上这个无赖没出息的方叶生,而舍弃他的。我突然伸出双手,用力拉住裤子,并且很坚决地叫道:“不可以!”我心里已经做出决定,要把自己的贞操献给真爱我的男孩——孙雁南。
方叶生有些惊讶,随即垂头丧气了。我马上穿好衣服,坐到桌子边,不看他,也不说话,内心里十分尴尬。他突然恶狠狠地抓住我的手臂,问我:“你是不是还在想着那个姓孙的家伙?”我没有说话,觉得在刚才他那样兴奋的时候,突然破坏了他的兴致很不好意思。过了一会,我说:“对不起,我不想这么早就做这个事情,我才16岁啊。”他也平静下来,问我:“那你以后还理不理我?”我点了点头,自己也说不清是表示理他那,还是不理他。
后来方叶生约我的时候,我竟然尽量找出借口不去赴约。不过只要去了,我对他亲我、摸我的动作没有丝毫拒绝。有一次,他拉着我的手去摸他的下体,我第一次摸到男人的那东西,硬硬烫烫的,还不停地跳动。对于他提出的性交要求,我开始是很坚决地拒绝,但是越到后来我越难以抵制住诱惑了。
自从那次在他家里发生那件事情后,我脑子里整天都在幻想着性交的情景,下体也细水长流了。可是几在这个时候,孙雁南竟然不给我写信了,我几年后才知道,他是试探我是否对他有感觉呢。
然而我是个很懒的人,他不写信我也就不写过去了,况且我这时候性欲旺盛,晚上经常偷偷手淫到好晚,精神很差。我惊喜地发现,我的乳房变大了一些,阴户上也长着稀疏的几根毛了。
方叶生摸着我的乳房也明显感觉到变化,要我解开上衣给他舔,我想这样反正也不会失去贞操,就让他舔,舔得我几次受不了,真想跟他真刀真枪干一场,但是我拼命抑制住了,因为快要放寒假了,我一定要等孙雁南回来。
快放寒假的时候,孙雁南写信给我了,他说他是打球摔伤了,并且告诉我回家的日期。我接到信后,内心里百感交集,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回信,我却装着不在乎的样子,我想这封信肯定有些刺痛他了,否则,他不会一回来就很敏感地捕捉到我和方叶生的事情。
(三)禁欲时代
孙雁南回来的时候,我们正在期末考,由于下午正好是我讨厌的数学,我没有参加。听班上的姐妹们说,看到他在教学楼上跟以前的哥们聊天,很高兴的样子。我想到自己和方叶生的事情,顿时觉得很龌龊。我知道他晚上会约我的,所以晚自习我请了病假。
他是被一个我很讨厌的叫陈姗华的女孩带来的,我心里很不安,不知道陈姗华跟他说了什么。他见到我一点都不激动,约我到操场上去走走。一开口,我就知道他已经知道了我的事情。他旁敲侧击地问我的生活,我一句都不说,心里在骂:“你这个笨蛋,说这些无聊的干什么?我为你留清白的身体到现在啊,快说正题吧!”可是在操场上转了几圈之后,他的心情越来越坏,把我送到寝室门口,说明天会去送我回家就要走了。我站着不动,心想即使晚上不约我出去,总得吻我一下才走吧?他看到我不动,走了回来,我心里砰砰直跳。谁知道他只是很温柔地说了一句:“进寝室吧,天冷。”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我知道,他对我很生气,尤其是我刚才一句他想听的话都没说,让他可能有些愤怒了。
我对他这样的呆子也很生气。所以第二天他送我的时候,我没要他送多远。
我看得出,他的眼睛有点红,昨晚肯定没有睡好。但是跟他走在一起,我备感压抑,他有点刨根究底的样子,恨不得要我承认错误。
他转身走的时候,我心里酸了一下,突然有了要根方叶生做个了断的想法。
所以,我直接上了开往方家的船。我告诉方叶生,我只爱孙雁南,我和他要正式分手了。他父母在家,他没有把我怎么样。而且我吓唬他,寒假开学的时候,孙雁南要找人打他,他这个胆小怕死的家伙,自此再也没有纠缠过我了。
寒假孙雁南打了几次电话给我,但是我讨厌他那种颐指气使的语气,后来就让我母亲去接,我母亲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,我则在旁边有些放肆地笑。孙雁南对我肯定很失望了,我们再开学时,他到学校去过,但是没有找我,后来一年都没有再写信给我。而我,不知道为什么,一年中也没有再跟其他男孩勾搭过。也许在我心里,觉得失去了孙雁南很可惜,我也很气自己吧。
高三一年,我的成绩滑到谷底。一想起孙雁南曾经鼓励我,要跟我在他那所大学的湖边约会,我便自我解嘲地笑起来。我几乎不怎么上课了,就喜欢睡觉。
白天一个人睡在寝室里,独自抚摩着自己虽不丰满但是很光洁的身体,心里很为孙雁南可惜,他别说摸,看都没有看过呢。学校终于不能容忍我的旷课了,劝我退学回家,和我一起的,还有盛余芳、占形燕等人。
由于退学时间是高三下学期,2001年的那个冬天可能是我最快活的时光了。虽然不再跟男孩鬼混,但是可以光明正大地逃课,玩累了也可以去教室看看。
元旦之前,我听说孙雁南写信给陈姗华了,心想莫非他们还有一腿?
我找人偷来了信,竟然很意外地看到,孙雁南在信里问到我的情况。一种跟他重修于好的想法诞生了,我马上买了一张贺卡,就写了几句很简单的话寄了出去。我明白,对于一个如此苦恋着自己的人来说,这样就足够了。果然,他回信了,说回来要来看我。
(四)花开花谢
孙雁南回来的时候,我们已经放假了,他也没有给我家里打电话,我以为他是敷衍我的。第二学期一开学,我就到学校去收拾东西回家,听到占形燕说,孙雁南在找我。他见到我,有点强颜欢笑的样子,我知道他没找到我之前,跟陈姗华谈了很长时间,也许陈姗华告诉他了吧。
他极力要我留下来陪他,他说他有好多话要跟我说。我明白,他想把我留下来的目的,是想在晚上占有我了。可是我跟家里说过当天回去的,所以反过来邀请他去我家。谁知道他胆子变大了许多,也不怕我母亲了,竟然真跟着我回了家,盛余芳和占形燕也顺便到我家去玩。
父母和哥哥隐约知道我跟他的关系,尤其是得知他是一所重点大学的学生时,都极为满意。我和盛余芳、占形燕商量,到他大学的那个城市去学电脑。但是,临到出发时,盛余芳被家人阻止了。
我和占形燕在哥哥的陪同下来到他的城市,却对那所在报纸、电台、电视上做广告的电脑学校大为失望,极力要求回家。孙雁南挽留无果,只好眼睁睁看着我们登上了回家的列车。后来,孙雁南多次打电话给我,要我再去那个城市,我有些心动了。况且,我明白,我留在家里,将永无出头之日。于是,我再次收拾行李,一个人来到县城乘车了。
(五)上错花轿
然而正当我在站台上等车的时候,我才发觉我站错了站台。而远处,从我目的地方向开来的反向列车正疾驰而来。我看到人群中有熟悉的脸孔,是我同班的几个女同学。她们极力约我去南昌去学电脑。错过了该乘的列车,我心烦得很,鬼使神差地跟着他们来到南昌。
天下的电脑培训学校都是一个样,如同天下乌鸦一般黑。到南昌,我们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,同来的几个姐妹被一些有钱人家的子弟泡了,一回来就跟我说她们床上的事情。而这时候,一个浙江的帅哥向我抛来了橄榄枝。失望加上寂寞,我开始和他约会,我们进展很快。
孙雁南千方百计地给我打电话,写信给我,我心已乱。为了他我坚守了三年清白之身,可是命中注定,他无法享用我的肉体吧。我开始逃避他,并很快和浙江的王霸诞上床了。
那天,王霸诞约我去他屋里看录象。说起来好笑,我们学电脑的,快半年了,都还不会上网,打字用拼音一分钟才十三、四个字,所以平时的日子很无聊。王霸诞的屋我们以前经常去,但都是几个人一起。那天我进去后才发觉,只有我们两个。
他放的是《玉女心经》,到性交镜头的时候,看得我脸红耳热,而他已经搂住了我,手从我衣下摆伸了进来。一年多了,突然重温被男人摸的感觉,我浑身如同触电一样,兴奋莫名。
我主动地和他接吻,他没来得及摸我下体就开始脱我衣服了。我手不由自主地伸向了他的下体,他兴奋地有些颤抖的声音说道:“好,让你看,对了,你用自己的手把它拿出来”说罢便以眼神催促着,这时的我已失去了理智,我将手伸向王霸诞的裤裆间,一抓,是那么硬,那么大……我慢慢的拉下了拉链,由内裤内将他的阳具掏了出来,看到那黑黝黝的那么粗大,还不停地点头,不禁吓了一跳。他不给我继续欣赏的机会,突然把我的脚用力张开,并开始舐我的阴部,因这姿势好像要尿尿的样子,我的脸红到了耳根,但是,好舒服喔……“你的乳头是粉红色的,是处女么?”王霸诞一口气把衬衫、裤子、内裤脱掉,一丝不挂的,骑到了我身上。继续抚摩了几下,他说道:“我受不了了,我要进去了”他粗硬的东西碰触着我花瓣的入口,终于来了,但,那瞬间,一阵激烈的疼痛。
“痛,好痛!”
“啊?你真的是第一次么?”我痛得眼泪都要出来了,没有说话。他缓缓的塞进来,粗大火热的东西完全的被包了进去。不知是痛还是热,我死命的抱紧王霸诞。
他边吻着我边说道:“晓平,放松一点,我动不了了。”他看我很紧张,用手指在我的小小乳房上画着圈,我感到一阵阵酥麻,不由得松开了手。我感觉到他的那根东西正慢慢的抽离我的下体,突然重重地插了进去,我“啊”地大叫一声,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让我的心好象要从胸膛了飞了出来。
紧接着,他像小鸡啄米一样,用很快的节奏在我的阴道里进进出出,我唿吸开始不畅起来,只好深吸一口气,然后重重唿出来,阴道里磨插的感觉让我忍不住想要大喊,但是我害怕别人听见,拼命咬住嘴唇。
随着他越来越快的节奏袭来,我感到无处发泄,张开嘴巴,朝着他肩膀狠狠的咬了一口。他“啊”地叫了一声,频率却更加快了起来,我感觉到自己正被带到高高的天空上去了。
突然,他重重地喘了一口气,趴在我身上不动了,我感觉自己猛然降到谷底,好一会才回过神来问道:“恩,你怎么了?”他有气无力地说道:“快要崩溃了,歇歇先。”我可不依,用力地抖动着下身,并疯狂地把他压到身下,自己抽动着。过了一会,他仿佛不甘被压迫似的,卷土重来,下面的那根东西更粗更热了,我快活地“哼”了几声,被他嘴唇堵住了,只得用手在他被上乱抓。
忽然,我感觉到他的东西在里面激烈地跳动起来,一种暖暖的东西开始大朵大朵地喷射,他低低地吼叫,我们用力相拥,想让这一刻停留更久。大约过了7、8秒钟,跳动停止了,但是他的东西还是硬硬地,好象伸长了许多,抵在我的身体内的某个地方,让我动都不想动。
他的那根东西终于慢慢软化了,被我的下体挤了出来,他把脸埋在我的两个不甚丰满的乳房间,嘟囔着什么,我暂时不想说话,也没理他。过了好一会,他从我身上爬起来,看了我下体一眼,然后吻了我一下:“谢谢你!”我知道他在谢我把第一次给了他,但我觉得他的表现不够热烈,问他:“会珍惜我吗?”他有些疲倦地点点头,说道:“好多血,我来给你擦干净吧。”我一翻身,有些害羞地说:“恩~~你转过去,我自己来。”他有些粗暴地略带戏谑地扳开我的双腿:“含羞什么,我刚才什么都看到了。”我捶了他一下,随他去了。他用手指拨开我阴唇,我感觉有什么东西立即流了出来,立即捂着脸,说道:“别这样……快擦掉啊。”他动作很温柔地擦了起来,一种痒痒的感觉传遍全身。我起身看被单,好大一滩血啊,不由得惊唿出来。
有了第一次之后,我的需求十分强烈。如果说看到被单上自己的血的时候,觉得对孙雁南还有一丝歉意,后来我就彻底在性天欲海享受了,差不多把孙雁南都忘记了。他当然不会这么容易忘记我的,接二连三写信给我,我回信告诉他,我们并不适合,如果他愿意的话,我可以做他的好妹妹。这封信彻底刺痛他了,他的回信十分愤怒,我正好就此不理他了。
和王霸诞几度消魂,但是他一直不肯把他房间的钥匙给我,反而只准我每个星期一、四去他那里,平时很难找到他。
快要放暑假时,我怕回家后与他很长时间做不了那个事情,就想天天呆在他一起。一个周末,百无聊赖地来到他房间时,看到门锁着的,正想往回走,忽然听到几声女人的呻吟。
这种呻吟我再也熟悉不过了,就是在性交很快乐时发出的,我不以为然的笑笑,却发觉好象声音是从王霸诞房间传出来的。我把耳朵贴在门上,听到里面果然有人在做那种事情,更要命的是,间或传出几声含混的说话声竟然就是王霸诞的。
我拼命地擂着门,心里的火苗一蹿三丈。里面有人问:“谁呀?主人不在里面。”竟然是那个女的在说话!
我更加火了:“你这个王八蛋,我听见你的声音了,给我开门!”王霸诞开门了,冷冷地看着我。我没有哭,只是一把抓住他的手臂,指甲恨不得穿透他的骨头。那个女的衣服还没穿好,一对丰满的白花花的乳房颤动着,很妖娆地走过来,说道:“怎么了?没看到过人家干事啊?来,王哥哥,我们表演给他看。”我愤怒地骂了一声:“贱货!”她扬起手掌,狠狠地打了我一下,然而王霸诞却事不关己地,走回房间坐下。我本想也给她一巴掌的,但是突然泄气了,捂着脸跑回寝室,把自己摔在床上。
第二天,我收拾好东西,谁都没有告诉就回了家。我是再也不会回到南昌那个伤心的地方了。